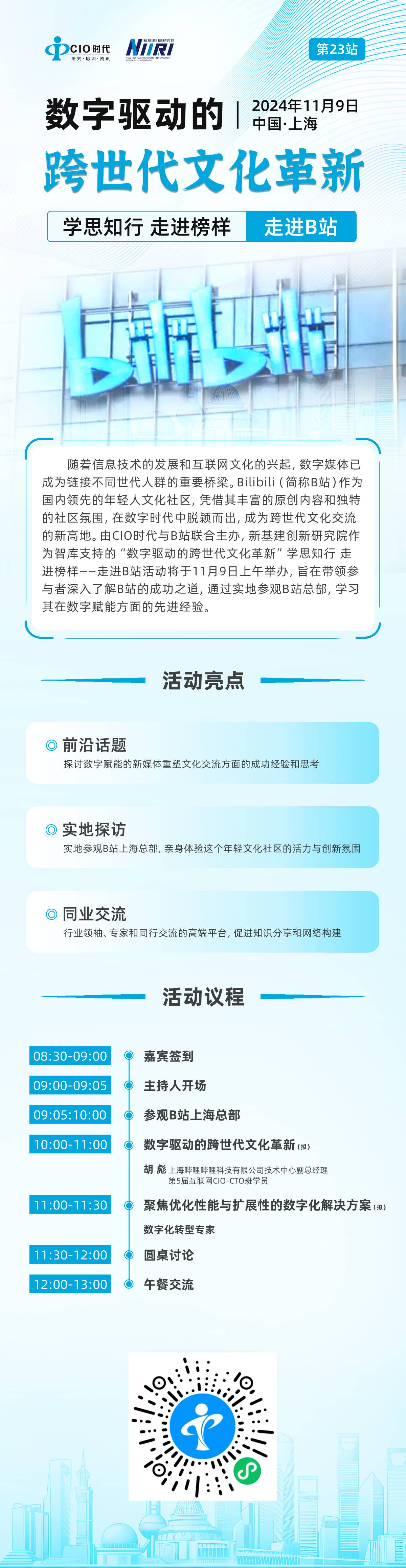记得这是无数个下午,电视频道定格在新闻台,音量调得很大,桌上常摆着隔夜的茶,在这样的环境里,爸爸却总靠在沙发上睡着,张着大嘴,手里握着遥控器,当我想调小声音时,他却突然醒来跟我说:“我听着呢。”
我是家里的独子,刚从学校步入社会,而我的父亲已经快70岁了。尽管他总是想尽办法在我的面前表现出一副很年轻的样子,想要竭尽所能隐瞒他的年纪,可是面对四楼的台阶时,他的腿和呼呼的喘气声还是替他说了实话。
之前我爸爸跟我说话不多,即便我早已成年,每当我想融入父辈的谈话时,他依然会扭过脸来说:“小孩子不要插嘴。”每到这时,我总能感受到来自父亲的威严,一种很强的压迫感,我便会乖乖地回到房间,把门锁上。
最近几年,我一直离家在外地,每次假期回家时,他都会拉着我坐上沙发,跟我讲一些他年轻时候的事,如数家珍的跟我普及属于他那个年代的特有的记忆,比如粮票,比如工分,再比如上山下乡。是的,他的话变得多了起来,脾气也越来越犟,常常跟他的老伙计们因为对国际局势的见解不同而吵得面红耳赤。
我知道,他怀念那个火红的年代,也怀念他年轻的时光。爸爸是名船工,记得小时候,我总骑在他脖子上,他驮着我站在远洋船的甲板上,卡带机里放着郑智化的《水手》,海风吹拂着我们俩的脸庞,几缕残阳被海鸥的翅膀斩断、剪碎,带着咸味的空气中夹杂着海浪卷来的泡沫,那个时候我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帅最可靠的男人,我一定要接他的班,成为一名劈波斩浪的水手。
海浪年复一年拍打着海岸上的砂石,剪碎残阳的海鸥一茬接着一茬,可是时光是回不去的。之前在他脖子上伸手喂海鸥的少年如今比他还要高出一个头,陪着他乘风远航的巨轮现在也早已退休成为了一个旅游景点在旅顺港静静地望向大海供游客参观,我最终并没有接他的班,但我跟那些水手一样,远离家乡,并定期返航。
港口还是那片港口,走近它,它便如时光一样漫无边际,离远看,它便缩小成一滴泪停留在这个苍老的城市之中。父亲也是这样,走近他,他不过是一个脾气暴躁的小老头,但在我每次离家时,他便成了撑起这个家的顶梁柱。我多么希望他能如这艘巨轮一样一直平稳的航行在这片汪洋中,任何风浪都不能使他倾斜,愿时光能放过他,我也想早点回家,再听他讲一遍他上山下乡的故事。